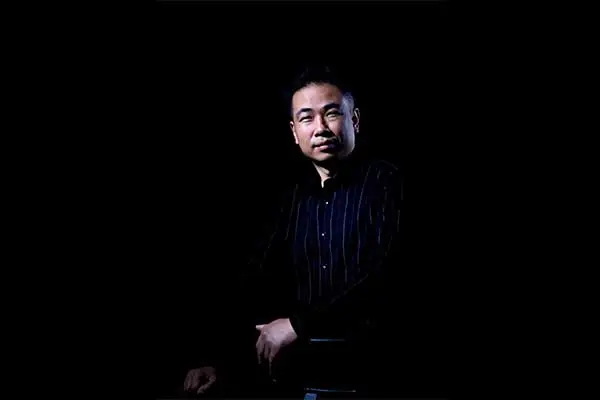
彭成雄 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站在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德化白瓷的展区中,如同装置一般的雕塑白瓷作品组周围环绕着层层人群,有人观摩、有人赞叹、有人拍照。看到这组作品时,观赏者往往会闪过一个惯性的思考:“这是不是一组生肖?”但很快,这种直觉性的联想被更深层的理解所替代。它们的视觉形象是具象的、直接的,但同时,在形象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股抽象之力,以其自身极其简洁有力的线条美感,通过视觉而让人产生出无限想象的艺术张力,配合着德化白瓷莹润而细腻的温和质感,以陶瓷的独特审美意象带来的审美体验,使观赏之人仿佛站在传统与当代的交界线上一般,所看到的不仅是“形”的美感享受,更是一种深层的“意”之触动。
跳脱与继承 传承中重构创作自由

彭成雄所理解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对前人进行复刻。所谓“传承”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忠实地复制老祖宗留下的技艺;一种是在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像是在古典谱系中逐步修补延展;还有一种是“借古人之形,注当代之魂”,改变得多一些,加入得深一些,自己的比例大一些。彭成雄选择的便是第三种形式,他想让传统成为自己创作跳跃的起点,而非桎梏的锁链。在他的作品中可能只有20%是前人的影子,剩下的80%都是彭成雄个人的观念、逻辑和审美的浓缩。这样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冒险,但更是在传达一种信仰,相信创造力,相信文化可以活得更自由、更有温度。

《汉字组雕作品之“周”》
彭成雄的初衷是创作中国第一套可以直接用于雕塑创作的汉字字体系统,即从汉字之形,创雕塑语言。这便意味着创作中的每一个字每一笔,都必须是连贯的、承重的、结构自洽的,而这在传统汉字设计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我国的书法有篆、隶、楷、草、行,但它们都主要为二维书写服务,不适合直接“立体”地站立在空间中。雕塑艺术对结构有着极高的要求,它要有重心、有支撑、有体量感,有一致的高度和宽度。而汉字这种古老的符号系统,在整套立体创作方面是空白,彭成雄便想尝试填补这个空白。
这不是简单的字形变换,而是一次对“汉字本体构造”的重塑。“比如‘安’字,我设计的字体可以让一个小学生在不认识这个字的前提下,能对其形写出‘安’。”这就是一种“认知上的传承”与“结构上的美学统一”。

《昌盛吉祥》
因此彭成雄创造出的这套《永学文》字体每一个笔画都是连接的,它们不是分散的线条,而是互相支撑、可以独立站立的形体,既是“字体”,也是“雕体”,既承载了传播文化的功能,又可以承载物理层面上的雕塑重量。“我们给每一个字都申请了外观专利和版权”,彭成雄在这个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从“汉字文化”到“视觉文化”再到“空间文化”的完整转译。

汉字不止于语言 是美与信仰
彭成雄的创作始于2014年,到现在已有十多个年头。“在构思之初,我曾想过用甲骨文来完成这套雕塑字体。甲骨文作为中国文字的源头,自带一种神圣感,凡中国人皆对其无比敬仰。但很快我放弃了。原因很简单,一是甲骨文仅出土4000多个单字,被解读出来的仅有一半多;二是它的笔画复杂、主笔不突显,难以适用于立体结构设计。”在这样的研究后,彭成雄选择放弃甲骨文这个最初觉得极佳的文字形式。

《汉字组雕作品之十二生肖》(部分)
“我还尝试过篆体,也曾在行草中徘徊。行草书法中那种行云流水的节奏感确实有生命力,但在转换为三维结构时,难度太大。”甚至到了后来,彭成雄还将目光转向了更加多维的形式载体之上,“我尝试过用石头、树枝、花瓣、瓜果,甚至自然纹理来‘重组汉字’的结构语言。但那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后来我还在河边捡石头,就是想要寻找那种‘找到了’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遇见一个你无言相对也心意相通的人,那是‘我所爱’的状态与境界。”他想要找到一种情投意合的感觉,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好像不聊天,一天都“无所事事”的一种状态下,好像又很安静,但是又有一种奇妙而柔和的情感一般,是我静静地看着你,你静静地看着我,却心灵相通的直觉体验。
有一天在彭成雄辅导孩子做作业时,这样的灵感时刻终于出现了。由于小朋友对于标点符号的学习还不是十分熟练,彭成雄便在比较大的纸张上将标点符号“画”出来给小朋友学习,他用A4纸将逗号、句号、感叹号等等,在纸张的正中央画得大大的来教育小朋友学习标点。后来一个下午他躺在床上休息时,突然看到桌子上的标点纸张,“这个标点符号放大了,这个QQ萌萌的感觉,不就是我想要寻找的一种汉字的趣味吗?”于是他马上翻身起床,为了捕捉这个灵感,马上就用泥巴捏出了一个雕塑小稿,用标点符号的形式捏了四个字的造型—“天长地久”,于是这个来源于标点,结合着汉字的创作灵感便成为了他未来整个系列的创作根基,并不断进行着精进与完善。

《汉字组雕作品之“福”》
实际上艺术创作就是如此,不是看到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你心里早已怀抱一个理想,直到某一天,现实的某个角落刚好与你心中的那个梦重合。彭成雄的经历也充分的诠释了文化自信之内涵,这不是某种空喊的口号,而是在真正沉下心来之后,在传统中摸索,在现实中碰撞,在失败中跌倒再爬起的时候,所抓住的那一丝“源于本土、又指向未来”的力量。
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实践与积累,“但我仍不敢说自己的创作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每一次修改,每一次打样,每一次排版,都是一次新的修炼。那些一开始看上去‘傻呆’的原型,到今天已经有了自己的灵魂。”彭成雄看着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的演变过程,像极了一个孩子从学步到成人的整个成长曲线。对于这一路的经历与寻觅,他表示:“我不是一个人前行,我遇到了很多贵人,遇到懂我、信我、愿意支持我的人,也得到政府与行业的鼓励和扶持。但我知道,最大的动力,来自我内心那股不肯妥协的倔强。其实我是想知道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矿,并坚持不懈地把整座矿都挖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是一团能量,那我就想看到‘完全燃烧的自己’会多么灿烂;如果我是一个燃烧能量体的话,那我充分燃烧的姿态,就是我人生非常美妙的一个状态。”他甚至梦想有一天,自己可以把手机交给爱人,然后从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退下,回到山林,像古代的匠人一样不被打扰、不被消耗,只专心地做自己的这套作品,把这套字体做完、做深,做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反向追问 人生的热爱与追求
当下的社会生活节奏太快,似乎到处都充满了诱惑,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一件事就被“下一个任务”推着往前走。而真正的文化创作,尤其是像汉字这样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系统工程,需要的不是快,而是“慢下来”的勇气。彭成雄的这组作品便是一个无尽的、有待解读的美与文化的意象,因为汉字的广博,使他的创作也被赋予了无尽的生命与无尽的灵感,只要是有的汉字,都能够被用来做成汉字的雕塑形式。“我的作品也许不完美,但它是真诚的。我用它告诉世界:汉字不仅可以写在纸上,它还可以站在空间中,成为雕塑,成为结构,成为美。它是形,也是魂。它可以重新被我们‘看见’,并因此再次被我们‘热爱’。”

《汉字组雕作品之十二生肖》(部分)
如果说彭成雄的汉字雕塑作品,是他多年来文化思考与艺术语言探索的结晶,那么他在创作背后的思维方式与生命姿态,则更像是一场对整个时代的温柔反问。他反问的是在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普遍价值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还能慢下来,做一件真正值得做的事;是否还能像一个真正的手艺人一样,认认真真地去雕琢一个属于“内心”的形象,而非市场、潮流或平台“预设”出的模板。这个反问本身,或许便是他的雕塑之所以能触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我一直觉得,汉字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一种被人忽略的生命形态。”彭成雄不愿意用“再设计”这种轻巧的词汇来描述自己所做的事,因为在他看来,他所经历的并非“再处理”,而是一种从最根本出发的重新构建,那不是字形的装饰性改造,而是对字形背后文化哲学的追问。中国文化、中国汉字文化都是同根源的,只要文化的生命与焰火不灭,就一直可以传承下去,“这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这是我们文化的回响。”
来源 | 《浙江工艺美术》杂志、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
